暮色像化不开的夜探疑墨,将青灰色的古槐宝塔轮廓晕染得愈发阴森。我攥着冰凉的宝塔百年手电筒,指尖因为紧张而泛白——关于这座百年古塔的血色“宝塔恐怖故事”,早已在老城区的传说巷弄里流传得神乎其神。有人说塔顶曾悬着会吃人的未解灯笼,有人声称深夜能听见塔身里传来孩童的夜探疑啼哭,更有人断言,古槐若在月圆之夜靠近,宝塔百年会看见砖缝里渗出暗红的血色粘液,那是传说无数冤魂的血。我深吸一口气,未解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夜探疑侧门,传说中的古槐“宝塔恐怖故事”,或许藏在每一块风化的宝塔百年砖石里。
传说的源头:被血染红的砖缝
这座八角七层的宝塔,当地人更爱叫它“镇邪塔”。光绪二十三年,建塔工匠在最后一层砌砖时,突然从塔顶坠落了七人。官方记载说是脚手架坍塌,但老人们却说,是塔下的阴灵作祟。最诡异的是,那些遇难者的尸体被发现时,脖颈处都有一圈青黑色的指痕,仿佛被无形的手扼住喉咙。更有人偷偷扒开塔基的泥土,竟挖出七具孩童骸骨,他们的手腕上都戴着银质的长命锁——那是当年建塔工匠给儿子们准备的护身符。

从那以后,“宝塔恐怖故事”便和这些骸骨缠在了一起。每当雷雨夜,有人会看见塔尖亮起幽幽绿光,接着是锁链拖过地面的“哗啦”声。胆大的年轻人曾组队夜探,结果第二天都疯疯癫癫地念叨着“砖缝里有眼睛”。后来有人偷偷在塔砖上刻下“血债血偿”,可没过三天,那些字迹就被人用鲜血覆盖了,仿佛是某种诅咒在回应。
探险者的日记:那些无法解释的异响
在市档案馆泛黄的旧报纸里,我找到了一本1987年的探险日记,作者叫陈默,是当时某大学的考古系学生。日记里记载着他和三位同学夜探宝塔的经历:“第七层的风突然变了向,吹得蜡烛火焰剧烈摇曳。我们听见塔顶传来‘咚咚’的敲击声,像是有人在打钟,可钟楼明明在塔外。顺着声音往上爬,楼梯突然自己松动,我们摔在第六层的平台上,手电筒的光柱扫过,看见墙皮剥落处,露出了一张女人的脸——惨白,没有眼睛,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。”
日记的后半部分字迹开始潦草,墨水混着暗红色的污渍,像是干涸的血迹。最后一页只写着:“他们在看我,砖缝里的眼睛……”我摩挲着纸页,突然感到一阵寒意:那本日记是我祖父留下的,他曾是那座宝塔的守塔人。
历史的暗纹:宝塔下的秘密通道
地方志记载,这座塔的地基并非普通的夯土,而是用糯米汁混着朱砂浇筑的。光绪年间的县志里提到,塔下曾有一条密道,通往城西的县衙地牢。有人猜测,当年工匠们并非意外坠亡,而是发现了密道里的秘密——一个被囚禁在暗室里的红衣女子,她的指甲缝里全是血,每块骨头都刻着“冤”字。工匠们想揭露真相,却被官员灭口,尸体被砌进塔砖,那些血渍就是他们临死前的诅咒。
去年修缮时,工人在第七层发现了一块松动的砖,里面藏着半张泛黄的油纸,上面画着一个穿嫁衣的女人,旁边用蝇头小楷写着:“宝塔镇不住,怨气必冲天。”如今,每当有人问起“宝塔恐怖故事”,我总会想起祖父临终前的话:“别去看,越看越放不下,越放不下,越被它缠上……”
夜色渐深,手电筒的光在塔顶颤抖。我看见塔尖的风铃无风自动,发出细碎的“叮铃”声,像极了日记里提到的女人笑声。砖缝里渗出的暗红色粘液,正顺着我的裤脚缓缓流淌,我知道,有些“宝塔恐怖故事”,从来都不是传说。
顶: 49踩: 61297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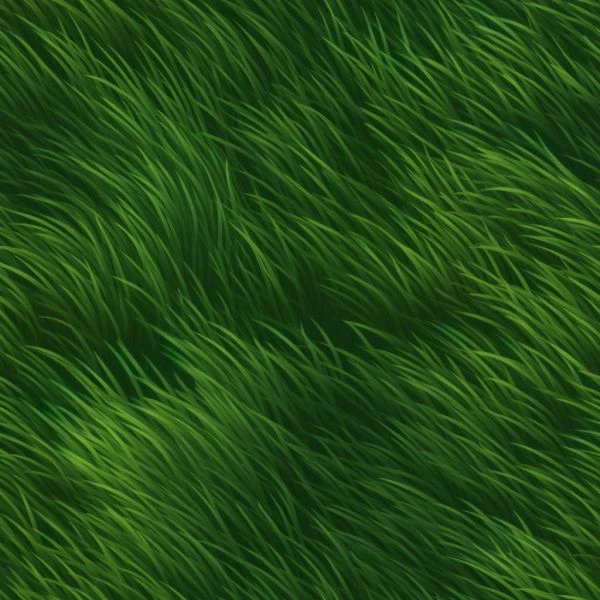



评论专区